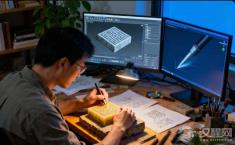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二
作者:翟屯建
二、徽派篆刻的发展(1644 —1848)
1.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文人篆刻由对篆法的研究,转而对刻法的重视,继又讲究篆刻合一,融笔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升华。
文人自有文人的优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归昌世、王志坚辈“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是极为痛快的。后来“三人为世故所驱,俯首干时”,①不再有刻印时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篆刻,由于有“刻”这样一种匠式操作过程在其中,似乎总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称篆刻为“雕虫小技”。但又总是抵挡不住方寸之间的那种无穷的艺术魅力,便想出点子说,篆刻的落脚点是“篆”而非“刻”,是学问而非技艺。明末清初之际,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对“字”的重视特别显现出来。对文字渊源流变、金文刻石的研究,成为篆刻理论和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注重考据。朱熹曾说:
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万历时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写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视为考据学的发端。歙县吴元满撰《六书正义》12卷、《六书总要》15卷、《六书泝源直音》2卷、《谐声指南》1卷,凌立撰《字镜》4卷,休宁詹景凤撰《字苑》,婺源游逊撰《字林便览》4卷。考据家钻研字学,是为研读经史,篆刻家钻研字学是为辨明书体,两者虽有侧重,但并不矛盾。吴元满同篆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经谈到。詹景凤虽没有篆刻方面的记载,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其孙詹吉工篆刻,有秦汉体裁,想必詹景凤也不会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县岩镇人程邃,“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对文字学的深厚学养,程邃借鉴钟鼎彝器款识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谓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规戒律,“合款识录(按:青铜器铭文)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②开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叶,徽州出现了不少金石文字辑录的著作。主要有江绍前《金石录》20卷,许楚《金石录》,吴玉搢《金石文存》,方成培《金华金石文字记》1卷,巴树谷《蟫藻阁金石文字记》1卷,吴颖芳《金石文释》6卷等。
虽有金石录,如不识金石上的文字,亦为枉然。乾隆以前,印学界对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递演变、缪篆与正篆的区别、官和私印章名称考订等方面,对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借鉴金石以提高篆刻艺术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斋印说》,谈到古玺时说:
朱文小印,文多不识,而章法、篆法极奇古,相传为秦印,朱修能定为
二、徽派篆刻的发展(1644 —1848)
1.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文人篆刻由对篆法的研究,转而对刻法的重视,继又讲究篆刻合一,融笔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升华。
文人自有文人的优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归昌世、王志坚辈“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是极为痛快的。后来“三人为世故所驱,俯首干时”,①不再有刻印时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篆刻,由于有“刻”这样一种匠式操作过程在其中,似乎总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称篆刻为“雕虫小技”。但又总是抵挡不住方寸之间的那种无穷的艺术魅力,便想出点子说,篆刻的落脚点是“篆”而非“刻”,是学问而非技艺。明末清初之际,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对“字”的重视特别显现出来。对文字渊源流变、金文刻石的研究,成为篆刻理论和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注重考据。朱熹曾说:
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万历时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写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视为考据学的发端。歙县吴元满撰《六书正义》12卷、《六书总要》15卷、《六书泝源直音》2卷、《谐声指南》1卷,凌立撰《字镜》4卷,休宁詹景凤撰《字苑》,婺源游逊撰《字林便览》4卷。考据家钻研字学,是为研读经史,篆刻家钻研字学是为辨明书体,两者虽有侧重,但并不矛盾。吴元满同篆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经谈到。詹景凤虽没有篆刻方面的记载,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其孙詹吉工篆刻,有秦汉体裁,想必詹景凤也不会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县岩镇人程邃,“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对文字学的深厚学养,程邃借鉴钟鼎彝器款识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谓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规戒律,“合款识录(按:青铜器铭文)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②开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叶,徽州出现了不少金石文字辑录的著作。主要有江绍前《金石录》20卷,许楚《金石录》,吴玉搢《金石文存》,方成培《金华金石文字记》1卷,巴树谷《蟫藻阁金石文字记》1卷,吴颖芳《金石文释》6卷等。
虽有金石录,如不识金石上的文字,亦为枉然。乾隆以前,印学界对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递演变、缪篆与正篆的区别、官和私印章名称考订等方面,对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借鉴金石以提高篆刻艺术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斋印说》,谈到古玺时说:
朱文小印,文多不识,而章法、篆法极奇古,相传为秦印,朱修能定为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