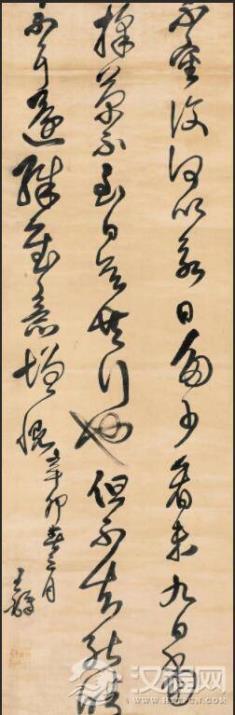书法的渊源与最早的书法形态-金文书法的风格分类
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以其所具有的上通天意的超验功能而占据“巫”文化的核心。在同一时期,金文也已经出现,但由于这个时期金文尚未获得“礼乐”文化的支撑,因而金文的发展处于被抑制状态。但应该看到,这个时期金文与甲骨文实际处于共生状态,二,则是由于金文尚未获得适合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金文与甲文的盛衰体现出两种不同文化选择的结果。
根据遗址发掘的情况,在盘庚迁殷之前商代彝器均无铭文,盘庚迁殷之后铭文开始少量出现,一般只有一到二个字,铭文图案化,装饰意味较浓,有典型的肥笔,大多为图腾、族徽符号。“这些单个字或合义式的金文,多刻铸在器物的内壁与底部等显眼处,位置既隐蔽,当然表明它不负担主要的功能。”殷商晚期铭文字数开始增多,但也大多为几十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而远远没有达到甲骨文那种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普泛程度,由此,整个殷商金文始处于受甲骨文支配的附庸地位。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根据遗址发掘的情况,在盘庚迁殷之前商代彝器均无铭文,盘庚迁殷之后铭文开始少量出现,一般只有一到二个字,铭文图案化,装饰意味较浓,有典型的肥笔,大多为图腾、族徽符号。“这些单个字或合义式的金文,多刻铸在器物的内壁与底部等显眼处,位置既隐蔽,当然表明它不负担主要的功能。”殷商晚期铭文字数开始增多,但也大多为几十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而远远没有达到甲骨文那种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普泛程度,由此,整个殷商金文始处于受甲骨文支配的附庸地位。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