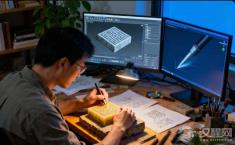“开宗立派”的文彭(1498-1573)
作为文征明的长子,文彭秉承家学,真、草、隶、篆诸体兼擅。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篆刻方面,开宗立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印学的一个新时代。
文彭(公元 1497 - 1573 年),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文征明之长子。因曾先后在南京、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故人称文国博。他少承家学,长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尤工草隶。他除 了学习文征明的书法外,还师法钟繇、二王、孙过庭、怀素,能融化各体、自成面目。《文国博(文彭)墓地铭》上说他“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过庭。而尤精于篆、隶、索书者接踵不断。往太史翁(指文征明)以书名当代,然有时不乐书,虽权贵不敢强。先生(指文彭)手不停挥,求者无不当意。”明人詹景凤说:“文彭篆、分、真、行、草并佳,体体有法,并自成家。”文彭虽曾学习父字,但终能
文彭(公元 1497 - 1573 年),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文征明之长子。因曾先后在南京、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故人称文国博。他少承家学,长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尤工草隶。他除 了学习文征明的书法外,还师法钟繇、二王、孙过庭、怀素,能融化各体、自成面目。《文国博(文彭)墓地铭》上说他“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过庭。而尤精于篆、隶、索书者接踵不断。往太史翁(指文征明)以书名当代,然有时不乐书,虽权贵不敢强。先生(指文彭)手不停挥,求者无不当意。”明人詹景凤说:“文彭篆、分、真、行、草并佳,体体有法,并自成家。”文彭虽曾学习父字,但终能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